建德乡村之所以能“生长”出一支又一支合唱团,得益于浙江多年前在乡村厚植文艺土壤、播撒文艺“种子”。时候到了,“花儿”自然朵朵盛开。而衡量乡村合唱团的成功,未必要看它获奖多少或登上过多大的舞台。当村民们在劳作时仍坚持练习、在唱歌里忘却生活的压力,甚至习惯了“回家做个饭,再来唱个歌”……当所有人挺起胸膛为自己而唱,那就是乡村合唱团最好的样子。
这是一个普通的午后,浙江省建德市三都镇镇头村没有发生任何新鲜事。如果非要说一件,那就是72岁的农民李玉英没去料理她的菜园,58岁的服务员周凤珍不在整理民宿的房间,42岁的家庭主妇洪娟没有钻进厨房准备晚饭……在镇头村文化礼堂的一间房间里,包括她们在内的十几位村民正坐在回字形会议桌边,挺胸抬头,双手叉腰,试图“找到”自己胸腔和腹腔之间的一块肌肉——横膈膜。

“对,就是这样,跟我一起发出‘嘶’的声音,嘶……”此时,一名头戴白色复古报童帽、风度翩翩的女士正中气十足地带领着她们练嗓。她叫周霞,虽然上了年纪,但不需要借助话筒就能让自己的声音填满整个空间:“感受你们的横膈膜在发力,注意气息的稳定!”
“嘶……”李玉英模仿着她,感觉自己化身成了菜园里的一条小花蛇。而当周霞用“哞”的一声来展示什么是鼻腔共鸣时,在场的村里人都忍不住笑了:“这不就是老牛叫嘛!”“对,就是要学牛叫!”周霞眉开眼笑,本来放在琴键上的双手舞到了空中,指挥大家一起练习。于是,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午后,镇头村文化礼堂内传出此起彼伏的“牛叫声”。
“里头是什么声音?”有外来人问。
“哦!是我们村的合唱团在排练呢!”一位村民回答。
“村里还有合唱团?”
“有啊!我带你去看看。”
欢迎来到乡村合唱团
在认识镇头村合唱团之前,首先要声明一件事,这支合唱团从成立至今,没有在任何一次比赛中获得过任何奖项,而且村民们目前还在努力“攻克”他们的第一首表演曲目——《镇头,是一个很乡土的村庄》,也就是镇头村的村歌。据不完全统计,全中国目前至少有10万多支合唱团,作为可能都没被统计进去的村里的合唱团,镇头村合唱团在全国几乎没有声量。
但这支合唱团有个响亮的名字——“铁姑娘”合唱队。在镇头村,“铁姑娘”是能被刻进村史的、掷地有声的三个字。1964年,那时镇头村还叫“镇头大队”。在遭受一场惨烈的旱灾后,当地决定修建镇头水库,11个大队共1000余人团结一致、艰苦奋战,历时多年终把水库建成。在那段充满奋斗豪情的时光里,大队的女同志白天在水库上搬石头,晚上组成“铁姑娘”队,用丰富的文艺演出为大家鼓劲打气,她们日后被视为“镇头大队”精神的缩影。
“她就是当年的‘铁姑娘’,还是队长呢!”合唱团里,有人指着李玉英介绍。两鬓已有些斑白的李玉英笑眯眯地点点头,她说:“我现在成了合唱团里年纪最大的成员。”
比李玉英小20多岁的黄爱娟在村里的民宿当服务员。“今天有客人一来就挑三拣四,说这个淡了、那个咸了,我们也只能尽量去满足客人的各种要求。”心直口快的黄爱娟跟团员诉说完工作中的烦恼后,眉头一展道,“本来觉得好像很累,但一来到这里我就不累了,跟你们在一起唱歌,我好像能把那些累的事情都忘掉。”
在大家聊天的时候,有一个人正忙前忙后,一会儿给大家发放新打印好的乐谱,一会儿招呼新来的成员选个离老师近点的座位坐下。“她是我们合唱团的‘文艺大师兄’,我们也叫她班长。”在其他人的介绍下,姜献君走了过来,她穿着笔挺的衬衫,精神头十足。“‘文艺大师兄’是要为大家服务的角色,我会通知大家训练时间,每次训练提前半个小时来开门,打扫卫生,把会场的设备调试好。”她说。
有人提起了一个叫红姐的人,但很遗憾红姐今天没来。“我们这里红姐唱得最好,但她最近去杭州市区带孙子了。”姜献君说。
十几位合唱团成员里,有养鸡的、种翠冠梨的、种西红花的、做服务员的……大家年龄不一,在村里各有各的生计和生活,但聚到一起后,就想着一件事:唱歌。但如果仅仅是喜欢唱歌,自己在家里唱唱就可以,为什么非要组一支合唱团?

“铁姑娘”合唱队在“渔舟唱晚”音乐会上演出。
“我们太想回到舞台上,继续给村民表演了!”李玉英说,这些年来,“铁姑娘”们一直很怀念十几、二十多岁时在台上表演的时光,参加合唱团是她们的夙愿。另一个契机则是去年浙江省举办的“我要上村晚”村歌大赛。镇头村早就有了自己的村歌,村民们既想参赛,又为难地表示,“没有专业老师指导,我们唱得不好”。那时,身为建德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的周霞,正好在镇头村担任“文艺村长”,了解到村民心声后,她决定帮助村民把合唱团组建起来。
“铁姑娘”合唱队不是建德唯一的乡村合唱团。在镇头村20多公里外的下涯镇之江村,有一支今年3月成立的“歌之江”合唱团,目前有成员40多人,最小的8岁,最大的72岁,平均年龄56岁。
“我们也想唱歌,您能不能教我们唱歌?”今年初,当新疆流行音乐学会秘书长、词曲作家吴核在之江村打造国风音乐原创基地时,50多岁的村民宋淑芬找到他,表达村民们想成立合唱团的心愿。
“你们要唱,我们就试着组织呗!”吴核答应了下来,但没太把这当回事。他想,估计村民们就是想玩玩而已,跟跳广场舞一样,把这当作一种消遣。那时他正好在创作一首新歌,因为旋律不是特别复杂,他决定让村民们试着唱一下。“我把谱子和范唱音频交给他们后,过了两天,我还在想怎么教呢,没想到他们已经会唱了,我才知道他们对这件事如此投入、如此认真。”吴核了解后发现,这支队伍里“藏龙卧虎”,有唱婺剧的农民、喜欢流行音乐的渔民、退休多年的文艺骨干……他们参加合唱团,不是为了随便唱一唱。
“我这才认识到大家的决心。”吴核告诉村民们,“欢迎大家来到合唱团,我们一定能把这支合唱团建好!”
为热爱排除万难
去年,在“铁姑娘”合唱队成立的第一天,周霞面试了十几位村民。她回忆,同样是唱一声“妈妈”,有的人的音在“十楼”,有的人的音在“三楼”,还有一些人在“地下室”,根本打不开嗓子。
“合唱是声音的艺术,首先声音要美。”她在排练室的黑板上写下“唱歌的六大基本功”“三大共鸣腔体”“六个共鸣腔位置”……决定从音准、节奏、气息到发声、咬字、共鸣腔体,一项一项地带领村民们翻越基本功的“大山”。
“歌之江”合唱团同样也在修炼基本功。自认为更擅长音乐创作而非演唱的吴核利用自己的“人脉”,给合唱团找来了两位“外援”老师——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市的歌手车翔和在安徽省芜湖市一家艺术培训机构当声乐老师的姚瑶。

“歌之江”合唱团在清晨的江雾中排练。受访者供图
车翔今年36岁,从年龄上看,合唱团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她的父母辈,但她爱管他们叫“孩子们”,因为她发现这群学生跟小孩子一样,眼神里透露着单纯与渴望。
她回忆,有一次,她在课上跟村民们强调,气息是万声之本,回家一定要好好练气。等到下一次上课的时候,一位50多岁的大姐像小朋友跟老师求表扬一样告诉她:“车老师,我昨天在田里干农活的时候,手里拿着锄头,嘴巴、鼻子没闲着,一直在练气!你看看我练得对不对?”
那一刻,车翔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她说:“我教合唱团有十多年了,但给村民朋友们教学是头一回。以前在给业余合唱团上课的时候,我会注意劲儿不要使大了,担心讲得太深刻的话,学生会烦。但在给之江村村民上课时,他们认真的劲头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必须尊重他们的学习态度,我必须帮到他们。”
为了给村民们上课,车翔买了航空公司的“随心飞”产品,定期从新疆飞到浙江。姚瑶也坚持每周日从芜湖坐火车到建德,跟村民们“一周一会”。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她们见证了村民们从一开始的“大白嗓式瞎唱”到学会正确呼吸、学会用优美的站姿站在舞台上,也看到了一些村民如何“为热爱排除万难”。
“村民们干农活的时候很辛苦,但他们还是会坚持来排练。一些人要帮子女照看小孩,有一次一位大姐直接把孙子带到了课堂上,但小孩子难免哭闹,她担心孩子影响大家上课,又抱着孙子走了。”回忆起那一幕,车翔觉得有点心酸。而让姚瑶特别感动的是,一些村民在无法到场训练时,会把需要排练的歌词、谱子、音频都提前要回去,自己找时间练习。
在合唱团成长的路上,年龄也是一道坎。“一些村民已经70多岁了,年龄越大,声音会越晃,声带在机能训练上没有年轻一点的姐姐好控制。有时候,一些人的高音上不去,我会悄悄在她耳边说,唱不上去的话,中间换下气也没关系。”车翔说。
这是不是意味着乡村合唱团的名头前永远会带着“业余”二字,没办法成为专业合唱团?
“不是的。”车翔说,“的确,从专业角度上来看,声乐是不可能速成的,村民们需要有老师长期指导,也需要持续练习,保持良好的歌唱状态。成为一支成熟、专业的合唱团的过程会很漫长,但并非不可抵达。”
周霞也常跟村民说,你们慢慢来。在镇头村村歌里,有一句“春绿的时候绿,秋黄的时候黄”。一开始,一些村民口音重,把“春天”唱成了“圈天”。“唱歌讲究咬字清晰,要练好字头、字腹、字尾,而一些村里人不太会说普通话,常把字腹丢掉了,比如把‘传统’唱成‘全统’。”周霞说,直到她指出来,村民们才发现他们一直是这样发音的。
“我们说了一辈子了,你叫我们怎么改?”一些村民表示很为难。那次之后,周霞转念意识到,也对,保留原生态的感觉,有点乡音才更好玩,乡村合唱团如果搞得和城里的合唱团一样那多没意思。所以她选择告诉村民:“不用改了,我们只需要稍微纠正到让人能听得懂就行。我不要求你们专业,我要求你们能快乐地展示自己,能在原来完全不懂或者只是爱好的基础上,学会看谱子、打拍子,唱得更规范,玩得更高级。”
作为音乐创作人,吴核也想尽办法,从“源头”上帮村民解决困难。“当村民们唱不好的时候,他们很容易第一时间质疑自己的能力。但我知道,一些歌村民唱不好,既有唱功的因素,也是因为那些歌本来就不是为他们而写的。”吴核说,“我始终认为,他们的那份兴趣和热情是最宝贵的。所以为了让他们在合唱时有更好的体验感,我会为他们量身定制歌曲,在写歌的时候,注意别把音乐跨度搞得那么大。碰到一些原曲太高的歌曲,我还可以用技术给他们降半个调,如果依然不好唱,我就帮他们重新编曲。”
如今,无论是“铁姑娘”合唱队还是“歌之江”合唱团都曾成功站上过舞台表演。同时,在不懈地追求着“专业”和包容自己的“不专业”之间,这些合唱团的成员们轻松地就找到了平衡。这或许是因为,对他们而言,唱歌的难从来不会难过生活的难,而就算唱得不好,能唱就足够快乐。
黄爱娟说起,这个季节,有时晚上排练完,天已经完全黑了,从文化礼堂走回她家大概要十来分钟,一路上她边走边哼着歌,觉得这一天过得心满意足。“我50多岁了,在这个年龄阶段,生活里难免有大大小小的压力和烦恼。但唱歌的时候,我离那一切都远了,此时此刻,我只活在一首歌里,那是只属于我自己的一处时空。”她说。
文艺土壤非一日之功
对于像黄爱娟这样的农村人来说,能在村里参加合唱团,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吗?
或许是的。只是这种奢侈未必是金钱层面上的,而是组建一支合唱团并把它长期运营下去,确实需要很多条件。比如,要有能牵头的人、有组织者、有可招募的成员、有供排练的场地、有指导老师、有音响设备、有经费……总之,这不是一拍脑袋就能做成的事。而在建德乡村,之所以能“生长”出一支又一支合唱团,是因为多年前浙江就开始在乡村厚植文艺土壤、播撒文艺“种子”,时候到了,“花儿”自然就一朵朵盛开了。
2013年,浙江在全省农村地区启动了文化礼堂的建设工作。2018年正式启用的镇头村文化礼堂正是浙江建成的第1万家文化礼堂,而它日后为村里乡村合唱团的排练和演出提供了场地。

坐落在镇头村的“乡村音乐学校”。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凌青 摄
2022年5月,浙江印发《关于开展“艺术乡建”助力共同富裕的指导意见》,提出通过开展“艺术乡建”,引领乡村文化发展。正是在“文艺家协会结对”“文艺村长”“艺术家驻村”等多种“艺术乡建”工作模式下,三都镇得以成为杭州市音乐家协会的“音乐创作基地”,与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合作举办乡村音乐会,邀请到包括周霞在内的音乐人、作曲家担任“文艺村长”,并建成“乡村音乐学校”,全方位唤醒村民对文艺的热情,也挖掘和培养了基层文艺人才。
2024年5月,浙江更是在全国首创“文化特派员”制度,要求文化特派员聚焦宣传文化工作,在所驻乡镇(街道)范围内重点指导1个行政村,结对1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或农村文化礼堂,开展若干项工作任务,服务周期为两年,每年要驻乡镇(街道)100天左右,每个月至少要赴基层指导服务一次。最重要的是,这些文化特派员是带着资源下乡的,其中,浙江会为每位省级文化特派员每年提供20万元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从“文艺村长”到成为杭州市级“文化特派员”,正是进一步的资源支持让周霞在开展工作时感到更加顺利。正如浙江首批省级文化特派员陈云感慨的一样:“有了这样的支持,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将文化种子播撒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还能确保这些种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真正实现以文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
除了省一级的政策和资源支持外,地方政府也积极在文化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课题上创新“解法”。
“没有吴核老师,就不会有我们‘歌之江’合唱团。合唱团的老师是他请来的,唱的歌是他创作的,排练场地和器材也是他提供的。”之江村的村民们说,他们打心底感谢这位从大西北过来的艺术家。而吴核之所以能与之江村结缘,要得益于建德的“乡村梦想家——我在建德有个村”招募工作。正是通过该项目,吴核入驻之江村,在运营经费、创业担保、税收优惠等方面得到精准支持,利用闲置4年的农房打造国风音乐原创基地,并招引全国各地的“圈内好友”来此采风创作。
“其实,相较于我创建了‘歌之江’合唱团的说法,我更认同合唱团的出现是一种自发的过程。首先是村民有了这个意愿,我们只是把握住了他们的真实需求。这种需求也不是外力生造出来的,而是天时地利人和下的水到渠成。”吴核说,“而我这样一个‘外来人’愿意在之江村扎根,也是因为感受到了这里有能滋养我创作的文艺土壤。所以,我们是互相成全。”

吴核在之江村打造了国风音乐原创基地。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凌青 摄
而文艺,当它作为一个人是否能选择的生活方式时,与经济基础或者说生活条件的好坏,也息息相关。在今天,农民宋淑芬能在闲暇时间钻研怎么用胸腔共鸣把《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唱出气势,而回想过去,她说家里连种田的肥料都是借钱买的,早上4点多钟就要去割稻子,只能把孩子带到田边去。“现在这样的生活是天上过的日子嘞!”在她的感慨背后,是多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农村经济全面繁荣、农民生活显著改善的成就。而对于吴核和妻子刘静这种曾常居北京的人来说,过惯了一线城市的生活,直接搬到村里住后,他们不但认为生活质量没有下降,反而更享受身处田园中的松弛感,这要感谢“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农村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
“我现在经常跟一些年轻人说,你们一定要到农村来看看,这里才是能让你们大显身手的地方。”吴核说,他相信,在像之江村这样的地方,年轻人是能待得住的。
“确实是这样。”在大西北长大的车翔说,她始终忘不了今年初第一次走进之江村时的感觉。“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那天,她仿佛看见清朝诗人高鼎的诗句就“写”在眼前。
这首歌给我们自己
虽然为村里的合唱团无偿投入了许多资源和经费,吴核却强调,“我自己也是受益人”。
“对于创作者来说,情感很重要。在村里,我能感受到城市里久违的人情味。”吴核说,平时他只要一出门,遇见的村民都会跟他打招呼,有些人还热情地邀请他去家中做客。“有一天,有个村民在路上遇见我时跟我说,吴老师,晚上来我们家吃饭。我以为他就是跟我客气一下,并没有真的去做客。没想到他后来直接打电话问我,吴老师,不是说好了来我们家吃饭吗,你怎么没有来?”吴核还提到,相处时间久了后,合唱团的成员也会跟他说,吴老师,你千万不要像别人一样,过一段时间就走了。
“我在这里观察到的、感受到的这些东西,滋养了我在艺术创作上的灵感。以前我们也经常出去采风,但那种蜻蜓点水般的体验完全没有真正在乡村住下后的体验来得深刻。”到之江村后,他接连创作了《阅与读》《江边小村》《钦堂在何处》等歌曲,创作灵感就来源于在村里生活的点点滴滴。
当他把这些歌发给合唱团成员时,他们在唱的时候会问,“吴老师,你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写?”“白墙描黛瓦,云中落烟雨,青石小路,留下幸福是足迹……”吴核一句句地跟他们解释《江边小村》的歌词,“你们看,‘白墙描黛瓦’写的不就是村里的房子吗?”
9月底,“歌之江”合唱团受邀去下涯镇的一场大型活动上表演《阅与读》这首歌。车翔在给大家讲解歌词内容时,也问了他们:“你们觉得这首歌唱的是谁呀?”他们很自然地想到:“唱的是之江村。”“错了。”车翔说,“这一首,唱的是你们自己。我们能力有限,能做到什么就是什么,你们把最好的自己展示给大家看就可以了。”当她说完这句话后,她发现大家再去唱的时候,眼里是湿润的,声音都变大了,胸膛也挺起来了。

“歌之江”合唱团开展日常训练。受访者供图
合唱团也把村民们带去了更大的世界。他们走出了之江村,走出了下涯镇,走出了建德市,到外地去演出。有次他们去杭州市余杭区表演,20多个成员在大巴车上激动地唱了一路。其实两地相距不过100多公里,但他们连连感慨:“想不到能去那么远的地方唱歌。”
合唱团又没有改变他们太多。也是在9月的一天,之江村迎来“艺术筑梦乡村”观摩团。按活动安排,村里的合唱团会在观摩会最后进行表演。可原本十点开始的会议,不知什么原因,略有推迟。时间来到了十点半,离演出开始大概还有一个小时,突然,合唱团里的两个阿姨跑到了吴核身边说:“吴老师,我们现在回去给家里人做个饭,马上就回来。”吴核心里没底地说:“能不能来得及啊?”他本想让她们表演完再回去,可阿姨们却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很快地炒两个菜就回来,保证不耽误演出。”吴核从窗户看着她们跑回了家。到了该合唱团上场的时间,他扭头点人,发现刚才请假的两个阿姨如约归队。他还能闻到她们身上的油烟味,一看,她们的手就是刚做过饭洗完后的样子,红彤彤的,似乎还透着油光。那天,望着舞台上大家认真大声唱歌的模样,吴核很想哭。亲眼看见过,他才确信,生活和音乐真的是在一起的,我可以回家做个饭,再回来唱个歌,这就是艺术最好的样子。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凌青

【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农民日报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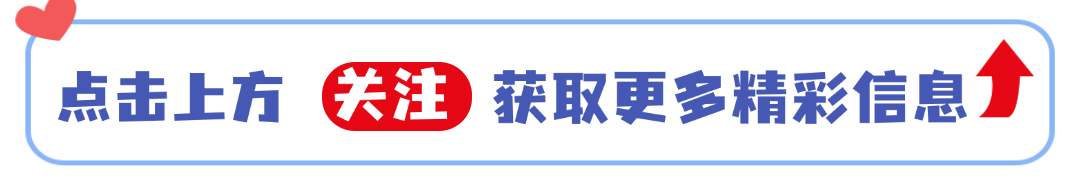


发表评论